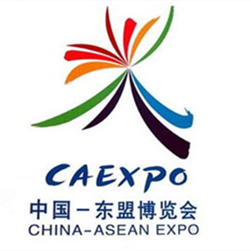可以感染古细菌的病毒smacovirus的示意图(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肠道中的古菌和人类疾病密切相关,但是在体内数量稀少,而且大多数无法在实验室内培养,所以很少被研究。而能杀死古菌的古菌病毒被研究的就更少了,迄今为止一共才发现了250种。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肠道古菌病毒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是不是有什么捷径呢?这可能得从我们这几年的老朋友CRISPR开始讲起。
古菌病毒,我手里有你相片!
CRISPR近两年被开发成了基因编辑工具,但它本来是细菌体内防御噬菌体的基因武器。
CRISPR是“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的首字母缩写。在细菌体内,CRISPR是一长串DNA序列,序列每隔一段是相同的,但是相同序列之间那段是不一样的。这些相同的DNA序列都是细菌的,但是这一段一段不同的DNA是噬菌体病毒的。每当细菌把入侵的噬菌体打败后,就会把噬菌体的基因切下来一小段整合在CRISPR里面,相当于留了一张噬菌体的“相片”或者是“档案”。

(图片修改自网络)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马迎飞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题为 metagenomic analysis reveals unexplored diversity of archaeal virome in the human gut 的文章。该工作首次对来自人类肠道宏基因组的古菌病毒进行了深入挖掘及全面分析,揭示了人类肠道中古菌病毒组的多样性,为人类肠道古菌病毒组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瞥。

(论文作者供图)
接下来我们看看科研团队通过这种思路,吉光片羽中如何管中窥豹,都调查到了什么。
肠道古菌病毒的“人口调查报告”
科研团队收集了2271个肠道宏基因组样品及6个公开的病毒数据库,把其中所有的CRISPR间隔序列(也就是噬菌体的基因碎片)全部收集起来,然后进行拼接和组装,再使用算法进行分类,识别出一类一类的病毒。所以下文需要注意,科研团队找到的病毒并非实际意义上的活病毒,而是通过分析得到的一条条病毒序列,故下文称新发现的病毒为“类”。
最终科研团队鉴定出了1279条古菌病毒的序列,构成人类肠道古菌病毒组数据库 (HGAVD) 。对HGAVD数据库中的病毒序列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大部分序列 (68.4%) 无法被分类到任何已知的病毒类别,表明人类肠道中已知病毒只是冰山一角,依然存在大量未知的古菌病毒。对于其他数据库已有的肠道古菌病毒数据,其中的大部分序列(83.3%)和类别(78.4%),在HGAVD中都能找到。
HGAVD收集到的数据别的数据库收集不到,说明HGAVD收集能力强;别的数据库收集到HGAVD也能收集到,说明HGAVD收集全面。HGAVD这份“调查报告”算得上是真实而全面的调查结果了,对肠道古菌病毒组具有良好的代表作用,极大地增加了肠道古菌病毒的知识。

肠道古菌病毒的鉴定(论文作者供图)
通过数据库科研团队发现一些有趣现象,比如人肠道的古菌病毒在男女之间没有差异,和人的胖瘦(BMI指数)也没有关系,但是和人的居住地有关系:例如7类病毒在亚洲、欧洲和美洲人群中经常能检测到,但是在非洲人群中较少检测到;而反过来一些病毒(例如smacovirus)在非洲和欧洲人群中具有更高检出率。
肠道古菌病毒绝大部分(n=1217,95.2%)都感染肠道中最常见的甲烷短杆菌。这种细菌能产生甲烷,甲烷又是屁的成分之一,如果你的肠道没有这些噬菌体杀死一部分的产甲烷菌,你猜你每天放的屁会不会增加呢。
在发现的一千多种古菌病毒中,最多是感染M. smithii古菌的,足足有47类之多。但是病毒也并非只感染一种古菌,大约三分之一的肠道古菌病毒都具有广泛的宿主范围,并不局限于单一古菌。
团队从1279条古菌病毒代表序列上还预测出了97,208个编码蛋白的基因,通过这些蛋白的功能,研究团队推测这些病毒的习性,比如可以推测出人类肠道中的真细菌病毒类似,温和古菌病毒在人类肠道古菌病毒中占据主体地位。
所以你看,科学研究绝不是靠金钱和人手蛮力堆出来结果的,马迎飞团队从CRISPR蕴藏的一点点“病毒碎片”入手,就能分析出这么多的结果。所以科学知识和奇思妙想是最有效的阅读工具,而生物的基因组就像一本厚厚的历史书,等着你去巧妙地解读。
参考文献:
1. Sorek, R., Lawrence, C. M. & Wiedenheft, B. CRISPR-mediated adaptive immune systems in bacteria and archaea. Annual Review of Biochemistry vol. 82 Preprint at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biochem-072911-172315 (2013).
2. Ignacio-Espinoza, J. C. & Sullivan, M. B. Phylogenomics of T4 cyanophages: Lateral gene transfer in the ‘core’ and origins of host genes. Environ Microbiol 14, (2012).
3. Grazziotin, A. L., Koonin, E. v. & Kristensen, D. M. Prokaryotic Virus Orthologous Groups (pVOGs): A resource for comparative genomics and protein family annotation. Nucleic Acids Res (2017) doi:10.1093/nar/gkw975.
4. Terzian, P. et al. PHROG: Families of prokaryotic virus proteins clustered using remote homology. NAR Genom Bioinform 3, (2021).
来源: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本账号稿件默认开启微信“快捷转载”
转载请注明出处
其他渠道转载请联系 weibo@cashq.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