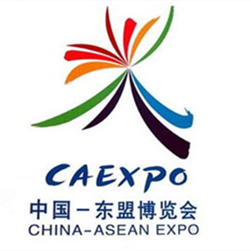宋江作为水浒传的绝对主角,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只有阎婆惜一个,宋江也是因为她跑路江湖,在外颠沛流离近一年时间,所以,阎婆惜是个值得一说的女人。
阎婆惜登场是在第二十一回,宋江送走了刘唐之后,趁着月色信步满街,忽听得背后有人叫声押司。宋江转回头来看进,却是做媒的王婆(到处都是王婆的身影啊),引着一个婆子,却与他说道:“你有缘,做好事的押司来也。”宋江转身来问道:“有甚么话说?”王婆拦住,指着阎婆对宋江说道:“押司不知,这一家儿从东京来,不是这里人家。嫡亲三口儿,夫主阎公,有个女儿婆惜。他那阎公,平昔是个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儿婆惜也会唱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岁,颇有些颜色。三口儿因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郓城县。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在这县后一个僻净巷内权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时疫死了,这阎婆无钱津送,停尸在家,没做道理处。央及老身做媒。我道这般时节,那里有这等恰好。又没借换处。正在这里走头没路的。只见押司打从这里过来,以此老身与这阎婆赶来。望押司可怜见他则个,作成一具棺材。”这里交代的很清楚,那阎婆惜年方十八岁,长得很漂亮,是个卖唱的行院,因为郓城县的人不喜风流宴乐,为什么不喜欢这调调呢?应该还是因为经济不发达,大家普遍都比较穷的缘故吧。所以,这一家三口就困在了郓城县,现在老头也死了,穷的连口棺材都置办不起,急切之间想要给阎婆惜找个婆家嫁了,这样就有人操办闫老头的丧事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但是死人也不能一直放着不埋葬,于是这王婆便带着闫婆找宋江来化缘了,宋江财大气粗,立马就个弄了一副棺材,还给了十两银子,让他们办理好闫老头的后事。
闫老头的时候事办完之后,闫婆发现宋江房里没有女人,就想着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宋江做妾,宋江有钱有地位,这闫婆日后也有了依靠,就找到王婆去说和,在王婆的一番操持下,宋江同意了,就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火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金玉。宋江这厮钱来得很容易啊。又过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却是为何?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这里说明了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有了裂痕,从如胶似漆到不待见,这个时间最少需要一个月吧。
一日,宋江不合带后司贴书张文远来阎婆惜家吃酒。这张文远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唤做小张三,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弹丝,无有不会。这婆惜是个酒色娼妓,一见张三,心里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张三见这婆惜有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净手,倒把言语来嘲惹张三。常言道:风不来,树不动。船不摇,水不浑。那张三亦是个酒色之徒,这事如何不晓得。因见这婆娘眉里眼去,十分有情,记在心里。向后宋江不在时,这张三便去那里,假意儿只做来寻宋江。那婆娘留住吃茶,言来语去,成了此事。谁想那婆娘自从和那张三两勾搭识上了,打得火块一般热。亦且这张三又是惯会弄此事的。岂不闻古人之言:一不将,二不带。只因宋江千不合,万不合,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以此看上他。自古道: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正犯着这条款。阎婆惜是个风尘娼妓的性格,自从和那小张三两个搭上了,他并无半点儿情分在那宋江身上。宋江但若来时,只把言语伤他,全不兜揽他些个。这宋江是个好汉胸襟,不以这女色为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张三和这婆惜,如胶如漆,夜去明来。街坊上人也都知了,却有些风声吹在宋江耳朵里。宋江半信不信,自肚里寻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自此有个月不去。阎婆累使人来请,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门去。这就是宋江和阎婆惜彻底决裂了,似乎差不多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那闫婆不知道是因为舍不得宋江的财力,不想失去这样一个金主,还是心中确实有愧于宋江,有一天就死缠烂打的把宋江拉到了家里,到了门口叫道:“我儿,你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阎婆惜倒在床上,对着盏孤灯,正在没可寻思处,只等这小张三来。听得娘叫道:“你的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婆娘只道是张三郎,慌忙起来,把手掠一掠云髻,口里喃喃的骂道:“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飞也似跑下楼来,就槅子眼里张时,堂前玻璃灯却明亮,照见是宋江,那婆娘复翻身再上楼去了,依前倒在床上。这个表现,已经是极端的不待见宋江了。阎婆听得女儿脚步下楼来了,又听得再上楼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儿,你的三郎在这里,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应道:“这屋里不远,他不会来!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来,直等我来迎接她。没了当絮絮聒聒地!”厌恶讨厌之情溢于言表,阎婆惜也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啊,不喜欢绝对不装不凑活,性格特征鲜明,只是不明白的她哪来的自信?宋江遇到这种情况,还不立马起身走人,磨磨唧唧的,不是个男人的做派,可能在心里对那阎婆惜依然还有几份幻想吧,进退两难,此时显得极为下贱。阎婆道:“这贱人真个望不见押司来,气苦了。恁地说,也好教押司受他两句儿。”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楼去。”宋江听了那婆娘说这几句,心里自有五分不自在。被这婆子一扯,勉强只得上楼去。原来是一间六椽楼屋,前半间安一副春台桌凳,后半间铺着卧房。贴里安一张三面棱花的床,两边都是栏杆,上挂着一顶红罗幔帐。侧首放个衣架,搭着手巾,这边放着个洗手盆。一张金漆桌子上,放一个锡灯台,边厢两个杌子。正面壁上,挂一幅仕女。对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
宋江来到楼上,阎婆便拖入房里去。宋江便望杌子上朝着床边坐了。阎婆就床上拖起女儿来,说道:“押司在这里。我儿,你只是性气不好,把言语伤触了他,恼得押司不上门,闲时却在家里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请得他来,你却不起来陪句话儿,颠倒使性!”婆惜把手拓开,说那婆子:“你做甚么这般鸟乱,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门,教我怎地陪话!”看来古往今来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即便是做了坏事,那也绝对不会承认的,现在很多出轨的女人,难道就是阎婆惜转世?宋江听了,也不做声,这里显得更加下贱。婆子便掇过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儿过来,说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话便罢,不要焦躁。你两个多时不见,也说一句有情的话儿。”那婆娘那里肯过来,便去宋江对面坐了。宋江低了头不做声。婆子看女儿时,也别转了脸。阎婆道:“没酒没浆,做甚么道场。老身有一瓶儿好酒在这里,买些果品来与押司陪话。我儿,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来也。”宋江自寻思道:“我吃这婆子钉住了,脱身不得。等他下楼去,我随后也走了。”那婆子瞧见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门去,门上却有屈戌,便把房门拽上,将屈戌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不是那虔婆要算计你,而是你心里实在舍不得阎婆惜娇嫩的身体吧?想要走,很简单,一脚踹开窗户,跳出去走就是了,这房子还是你出钱租的呢,你怕什么?
且说阎婆下楼来,先去灶前点起个灯,灶里见成烧着一锅脚汤,再凑上些柴头。拿了些碎银子,出巷口去买得些时新果子,鲜鱼嫩鸡肥鲊之类,归到家中,都把盘子盛了。这闫婆出去买东西,最少也要用时半个小时吧,宋江既然还是很下贱的待在房子里,真不知道他好汉的名声是哪儿来的?此时的景象,完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舔狗模样,想必读者老爷们看得也很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