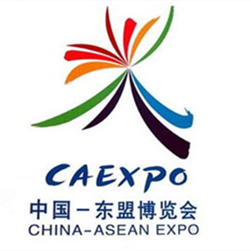▲俯瞰云雾间的219国道云南怒江美丽公路段(无人机照片)。 江文耀 摄
一
七月初,从蜀地一路疾驰,直奔彩云之南。
高黎贡山,这座我在心中默念了无数次的山,近在眼前,高耸云端。不敢高声,怕惊动了山间那一团团漂浮的白云。我惊喜地打量着窗边的山色,一串串芒果,闪耀黄色抑或紫红色的光泽,点缀着苍翠的山林。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3月28日在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拍摄的怒江第一弯(无人机全景照片)。
突然下起了暴雨,温度瞬间下降,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汽车雨刮器上下翻飞,在拼尽全力开启前行的路。窗外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突然一座“天桥”映入眼帘,气势巍然,撼人心魄。
原来是到了龙江特大桥。它横跨于龙川江之上,隐入雨雾和云端,是亚洲山区跨度最大的钢箱梁悬索桥。一桥飞架天堑,在高黎贡山和边城腾冲之间,它传递出造桥人的生命温度,也无声地讲述着令人骄傲的中国故事。
雨渐渐变小,薄薄的云烟从龙川江上升起,把“天桥”衬托得愈发雄伟。
大桥那边就是腾冲了,只需短短几分钟,就能踏上那片热土。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马背上的腾冲从未沉寂。此刻,仿佛一阵阵清脆的响铃声穿透渺远的历史天空,在我的耳畔回响。
过腾冲市区后,就到了和顺古镇。中国人对地名尤其讲究,这“和顺”二字,必是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祈愿和祝福。眼前的风光一如江南胜景,远山青黛若玉,近处溪流潺潺;田野间阡陌纵横,荷叶田田;而那些或红或白的花簇,就像古镇戴的发箍,透出万千风情。
站在高处眺望,古镇建筑依次层叠,向上铺陈。一条条灰白色的小巷子,就像古镇的经脉,疏密有间。人群熙熙攘攘,涌动而过,那些火山石砌就的照壁或城墙,也因此而灵动起来。
傍晚时分,古镇人家炊烟袅袅,远来的游人围坐嬉闹,烟火气息与欢声笑语交织融合,与远山近水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一幅山、水、城、人和谐相依的画卷。
二
翌日清早,又下起了滂沱大雨,叠水河呜咽,伴随我们一路前行。
叠水河畔、来凤山北麓,滇西抗战纪念馆宛如腾冲的眼睛,凝望着那段惨烈而悲壮的历史。1942年的滇西,究竟有多少中国远征军魂断异乡,又有多少腾冲人民血洒疆场?“若我马革裹尸,望汝善侍高堂……”一封封泛黄的家书,一把把生锈的刺刀,一顶又一顶弹痕累累的钢盔,仍在诉说那段血与火的悲壮。这一切,怎能不令人潸然泪下、肝肠寸断?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战前的腾冲,人口有26万,战后仅余14.5万余人……”讲解员沉痛的声音直击人心,令人久久难以平静。
纪念馆转角处,是奔腾不息的怒江。当年中国远征军在这里拼尽全力,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滔滔怒江,如同一匹野马,奔腾着,咆哮着,一遍遍拍打着血红的土地,激荡起层层回响。
1942年5月,日军占领滇西怒江以西地区,切断抗战时期重要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1943年10月,为重新控制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与英、美军队联合发起对缅北、滇西日军的反攻。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兵锋直指腾冲。
画面就这样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湍急的江流之上,是日军猛烈的炮火。密集的弹雨之下,一艘艘竹筏和橡皮艇紧紧相连,成为中国军人强渡怒江的浮桥。一个人倒下了,另一个人又冲上去……鲜血染红了怒江。
强渡怒江战役,历时近2个月,中国军队成功于缅甸北边建立桥头堡,日军则在反攻无力下退守中缅边境之外的龙陵松山,日军第一道防线终于被突破,滇缅公路战略通道重新被打通。
在这里,高黎贡山不再是绿色的,鲜血浸透了森林。
在滇西抗战的战场,中国远征军从怒江西岸攀上绝壁悬崖,每天在丛林弹雨中艰难行进数百米。
雨季的高黎贡山,气温骤降,瘴疠横行,因饥饿、疾病,以及夜间作战路滑坠崖等,官兵们有一半人失去生命,他们的遗体被就近掩埋,从此与高黎贡山永远相伴。
密林深处,骡马难以通行,官兵们只能把粮食、弹药等扛在肩上,哪怕勒出了血印。没有吃的,他们就挖野菜、啃树皮。
正是在这个时候,腾冲人民伸出了温暖的手,深深的军民鱼水情,让官兵们的心和腾冲人民紧紧相连。
“马帮”首领李正芳和族人做向导,带领远征军穿越日军封锁线;男人们抬着竹筐,女人们背起背篼,把粮食和药品等悄悄运到前线。一个雨夜,一支由300名妇女组成的队伍,在运送弹药时不幸摔死17人;腾冲自卫队员们骁勇作战,在高黎贡山北麓袭击日军运输队,烧毁其粮草储备,迫使日军分兵防御,减轻了远征军的压力。
军民同心,携手抗敌,最终中国远征军取得了高黎贡山战斗的胜利。被形容为“鸟难飞过”的大山,被官兵们踩在了脚下;他们在绝境中以血肉之躯开路,被美军顾问称为“山地战的奇迹”。刻在岩石上的“还我河山”几个大字,成为滇西抗战中“铁血精神”的具象化见证。
在这里,腾冲的古城墙不再是灰白色的,鲜血染红了一砖一瓦,一山一石。
1943年9月,年逾花甲的“抗日县长”张问德面对日军“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的劝降书,严词以对,写下传世名檄《答田岛书》。“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对于阁下所将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书信中历数日军侵略罪行,大义凛然,铁骨铮铮,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抵御外辱,保家卫国,腾冲人凝成了一股绳。学生们抬担架、送药品,组成“童子军”,当15岁的学生董春和倒在日军的枪口时,他的胸前仍紧紧抱着弹药箱;乡绅刘楚湘变卖田产,购买武器支援游击队;腾冲妇女会组织“缝衣队”,为官兵们日夜赶制棉衣,哪怕双手冻裂仍不停歇。
1944年8月,中国远征军开始围攻被日军占领的腾冲城,与日军在这座石头小城中展开激烈巷战——“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垣”。9月14日,中国远征军攻克腾冲,日本守军全军覆没。
正义必胜!滇西抗战纪念馆里,每一张照片都是铁证,日军的罪恶行径,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过“中国远征军名录墙”,近130米的墙体上,103141个名字依次排列,从中国远征军到盟军官兵,从地方游击队战士到参战民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不朽的英魂。
三
直冲云霄的高黎贡山,当它从那场噩梦中苏醒,几度春风起,野草又蓬蓬勃勃地长满山崖。
一条条宽阔的路,一座座长长的桥,无不承载着英烈们美好的希冀。山里和山外的距离已不再遥远,芒果的醇香和甘甜,让更多人品尝到了腾冲的味道。
高楼、霓虹灯、广场……如今的腾冲,是一座现代化的边境小城,绿水青山的生态,舒适宜人的气候,吸引了各地的人们前来游玩、定居。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怒江州贡山县雾里村盛开的樱花与远处的高黎贡山相映成趣(3月27日摄)。新华社发(彭奕凯 摄)
“小巷深几许,老屋苔色青。山村读书楼,古道风雨亭……山养心,水养性,桃源仙境……”市区西南处的和顺古镇宛如一幅静谧的水墨画卷,温润地抚平了一座城市的战争创伤。
“耕读传家远,书香继世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我走进和顺古镇的文昌宫,这里还保存有“和顺两朝科甲题名碑”,记录了明、清两朝取得过功名的和顺人计809人,其中举人8位,秀才600余位,在朝廷任过职官者180多位。数百年来,私塾、义学、女子学堂等,在此蔚然成风。
走进中国传统村落水碓村,跨上高高的台阶,就走进了和顺乡村图书馆,这是我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之一,1928年由华侨集资兴办。馆内现有藏书13万余册,分设古籍、民国、现代三个书库,典藏文献丰富而珍贵。
腾冲的文脉书香,并未在战火中消逝;腾冲的铁骨脊梁,在战火中愈加挺拔。19世纪70年代,法国被普鲁士占领时,法国作家都德曾写下著名的《最后一课》。1942年5月8日,腾冲即将被日寇占领时,时任和顺乡益群中学校长的寸树声先生,在和顺文昌宫集合全体师生,上了中国版的“最后一课”。他说:“你们要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炼你们的精神,在斗争里发展你们的力量!我相信,每一个黄帝的子孙,是不会当顺民的,是不甘心做奴隶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是和顺古镇的骄傲,他原名李生萱。在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革命事业中,艾思奇倾尽毕生心血,致力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他的故居前,一片竹林迎风而长,一池清水碧波荡漾。
腾冲的山总是那样苍翠,松杉葱郁,古树参天;腾冲的水总是那样清澈,水草簌簌地飘摇,自在而闲适。
千百年来,这似乎就是古城本来的模样,宁静而从容。在那一扇扇透着灯光的客栈或民宿里,或许马帮的人和像我们这样的旅行者住过,来了,又走了,把腾冲的念想带向远方。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 |周芳 魏秒
制作 |石建杭
来源 |中国民族报
觉得有用,点亮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