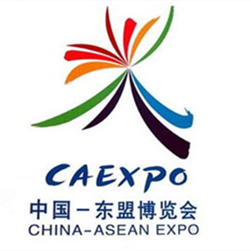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医保个人账户的改革是重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之所以称之为重点问题,是因为目前我国的基本医保资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二者比例约为3:1,后者占比并不小。但是,按照此前中央和各统筹地区的相关政策,医保个人账户只能支付个人的一般门诊医药费用,难以发挥医保资金的统筹功能,也不符合医疗保险“保大不保小”的基本原则。截至2021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存达3.6万亿元。其中,近40%是个人账户结余资金,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
之所以称其为难点问题,是因为改革面临的阻力较大。很多参保人认为,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是私人财产,应当由个人自由支配,医保政策的变动不能触动个人的财产权。从表面上看,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争议焦点是其法律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资金使用归属权;深层次观察,此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参保人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博弈,应从团体利益的社会法本位价值去寻找该问题的答案。

政策初衷是风险分担
从法律释义学的角度审视医保个人账户的性质和权利归属,恐怕无法获得确切的答案。社会公众对医保个人账户的理解主要来自于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44号文”),该文件第四部分“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中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且“个人帐户的本金和利息归个人所有,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
在此文件印发之前,国务院各相关部门也出台过包含类似内容的文件。例如:原劳动部印发的《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的意见》规定:“职工个人医疗保险专户金,为职工个人所有。”原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规定:“个人医疗账户的本金和利息为职工个人所有,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在“44号文”印发之后,很多地方法规也规定了医保账户的使用细则。例如:《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条例》规定:“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属于个人所有。参保人死亡的,其个人账户余额可以一次性支付给其继承人,没有继承人的,划入统筹基金;从业人员跨统筹地区流动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转移使用,无法转移的,其余额应当退还本人。”这些地方性文件增强了医保个人账户制度的可操作性,也更加强化了参保人对账户资金个人财产法律性质的认识。
按照最初的设想,基本医保统筹资金应通过当期的收支平衡法则实现参保人群体横向的风险分担,即在一个统筹年度内,将筹集来的保费支付参保患者的医药费用;个人账户通过长期的收支平衡法则实现参保人个人纵向的风险分担,即在参保人年轻、疾病风险低时多缴纳保费,少支出医药费用,老年多病时不缴纳保费,多支出医药费用。
但这个初衷在实践中未能很好落实。主要问题出在参保人个人账户中积累了大量资金,或由于个人的短视引发较高的道德风险,不仅让监管工作压力倍增,而且统筹功能难以发挥,对真正需要医保制度解决高额费用的参保患者不公平。社会各界对医保个人账户诟病较多,都在积极寻求改革方案。2010年印发的《社会保险法》并没有写入医保个人账户制度,为后续的改革预留了立法空间。
权利归属需综合判断
按照法律的位阶关系,从适用方面,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优先于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因为前者针对的事项更明确具体;从效力方面,后者高于前者,因为后者的颁布机关由人民代表组成,具备更直接的民主正当性。那么,《社会保险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是否应当以“44号文”的规定为准?答案也是不甚明晰的。国务院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名称包括条例、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实施细则等,按照《立法法》第3~5条规定,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可以直接作为法院审判的法律依据。但是“44号文”采用的名称是决定,一般用于构建专项制度的框架结构,带有纲领性政策文件的特征,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行政法规,只能视为国务院发布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按照《立法法》第6条的规定,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其他规范性文件需要经过合法性审查,才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鉴于“44号文”没有经过此审查程序,因此,相关规定也不宜直接作为医保个人账户法律性质的来源,其权利归属还要结合参保人意愿、资金使用情况、政策导向等因素综合判断。
平衡个体与团体利益
基本医疗保险系社会法法律制度,应当将团体利益作为本位价值。在立法部门划分方面,传统强调公权力本位的公法和私权本位的私法之间,形成了一个以同质化的个人组成的团体为本位的法律部门,即社会法。在工业社会,人们生存居住的环境呈现出同一化的特征,医疗技术和治疗方案也在规范的基础上趋同,建立在劳动关系基础上的劳动者在组织结构上整齐划一,这为建立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支付机制奠定了基础,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得以在社会法的本位理念下构建。
社会法强调社会和公共利益的独立性以及对特殊个体利益的倾斜性保护。在这个法律部门中,基于同质性特征形成的个人集合,即团体成为权利主体,作为传统私法主体的个人成为义务主体。作为传统公法主体的国家演变成为个体和团体利益的平衡者和维护者,不直接介入社会法的法律关系中,而应当通过建立平等的参与机制和协商机制,促进团体利益实现,最终将利益落实到那些需要给予特殊保障的群体上。
具体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上,立法和行政的职能应当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公权力筹集资金,并将资金用于更加弱势的大病患者的医药费用上。与之对应的,将资金作为参保人的个人储蓄,用于抵御个人老年时期高疾病风险的制度系传统的私法制度,与作为社会法的基本医疗保险法的立法本位不相容。
当然,即便是社会法制度,也不能脱离国家的积极作为。尤其在我国基本医保领域的社会自治机制还不甚完善的条件下,政府的立法和执法职能应当以更高的标准要求之。笔者建议,一方面,应当更合理地平衡参保人的个体利益和团体利益,在当前中央和各地方政策已经形成相对固化的制度和公众认知的情况下,改革还需要缓步推进,避免过激的社会反应。而且还要考虑出台必要的配套措施,比如优化“双通道”购药流程和“单独支付”药品保障机制,增强门诊慢病患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还应当完善社会协商机制和政策宣传机制,参保人与政府并非对峙和利益博弈的双方,政府更应当居于个人和参保人群体之间,为二者构建一套平等和谐的沟通程序,让双方主体充分了解和理解对方的需求和诉求,让立法更加民主、更加科学。同时通过各种媒体加强政策的宣传,及时打破谣言,疏导争议,为政策的落地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 娄宇
编辑:连漪 李诗尧
校对:马杨
审核:徐秉楠 王乐民